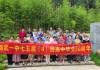?文字與圖像相生共舞
——評陸永建的《飛翔的痕跡》
伍明春

閱讀陸永建先生的《飛翔的痕跡》,筆者不由地想起香港攝影家陳復(fù)禮先生1979年到1990年創(chuàng)作的“影畫合璧”系列作品。所謂“影畫合璧”,就是攝影家邀請吳作人、李可染、劉海粟、李苦禪、關(guān)山月、程十發(fā)、趙少昂、董壽平、吳冠中、黃永玉等重量級書畫家,為其攝影作品添加一些因自身條件限制攝影而無法捕捉的意象(如遠(yuǎn)山、古松、仙鶴等),讓畫面顯得更靈動、更豐富、更具藝術(shù)感染力。“影畫合璧”作品體現(xiàn)出一種鮮明的“跨界”的特點。《飛翔的痕跡》一書所收的作品,顯然也具有這種“跨界”的特點。不同的是,“影畫合璧”中涉及的攝影和繪畫同屬視覺藝術(shù),且以攝影為主、繪畫為輔,換言之,繪畫只是其中的一種表現(xiàn)手法的運用,其最終整體呈現(xiàn)的效果是攝影藝術(shù)作品的形態(tài);而《飛翔的痕跡》中的散文作品和攝影作品,則跨越了語言藝術(shù)和視覺藝術(shù)兩個范疇,二者既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又同時構(gòu)成一種相得益彰的互文關(guān)系,進(jìn)而呈現(xiàn)為一種全新的文學(xué)樣式。作者本人將這種新的文學(xué)樣式命名為“攝影散文”:“把攝影作品和散文作品組合在一起,稱為攝影散文,它是影像技術(shù)高度發(fā)達(dá)催生下的一種新的文學(xué)形式。”在作者看來,這一新型的文學(xué)樣式的主要特征是:“力圖用哲學(xué)的思考、詩化的語言、精美的圖片,來表達(dá)我眼中、心中的人生和世界。”從這里不難看出,哲思、詩語、美圖是構(gòu)成一篇“攝影散文”的三大要素。
值得指出的是,在《飛翔的痕跡》一書中,文字和圖像的結(jié)合方式,既不同于傳統(tǒng)文學(xué)插圖那樣對文字做一種簡單的“圖解”,也不同于當(dāng)下讀圖時代那種拼貼雜陳式的并置(如互聯(lián)網(wǎng)網(wǎng)頁上的文字、圖片、影像結(jié)合,就是典型例子),而是二者相互生發(fā)、相互映襯的關(guān)系。譬如,作者在《城市與鄉(xiāng)村》中這樣寫道:
城市從鄉(xiāng)村中娩出,長大;但不會退化為鄉(xiāng)村,哪怕它像樓蘭一樣被沙漠吞噬,在風(fēng)沙中干癟,也決不后退。
鄉(xiāng)村渴望城市的富足和繁榮,城市向往鄉(xiāng)村的寧靜和放松,人生就在城市和鄉(xiāng)村的角色換位中升沉,文明就在這種升沉中延伸。
作者在這里沒有輕易地采取一種現(xiàn)代知識分子常用的批判立場,而是以一種更為開放、包容的視角來思考當(dāng)下城市與鄉(xiāng)村之間的微妙關(guān)系,并由此提升到對人類文明嬗變的思考。我們看到,與這篇散文文字相對應(yīng)的兩幅攝影作品,分別是西南古城貴州鎮(zhèn)遠(yuǎn)的夜景和福建周寧的鄉(xiāng)村風(fēng)光。也就是說,作者沒有選擇現(xiàn)代都市的摩天大樓,并以之與鄉(xiāng)村景觀形成鮮明的對比,而是有意表現(xiàn)了城市與鄉(xiāng)村之間的某種交融性和過渡感,此舉與散文《鄉(xiāng)村與城市》中所表達(dá)的觀念是一致的。
文字和圖像的相生相映關(guān)系,同樣在《黑格爾的貓頭鷹》一文和相應(yīng)的攝影作品中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面對當(dāng)下的人們沉湎于感官享樂、疏離哲學(xué)思考的普遍狀況,作者發(fā)出了如下批判和質(zhì)詢:
如今的夜景工程,把黑夜變成了白晝;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使人夜不思?xì)w,樂不思蜀。晝夜不分,黑白不分,使人類失卻了比名利和權(quán)貴更重要的精神活動。
哲學(xué)開啟了人類的智慧之窗,哲學(xué)照亮了人類的精神生活。
如果沒有哲學(xué),人的生命就會索然無味;如果沒有哲學(xué),人的靈魂就會黯淡無光。
何時,黑格爾的貓頭鷹還能在黃昏時起飛?
其實,作者就像一只在黃昏時分展翅起飛的貓頭鷹,盤旋在高空中,以深邃而銳利的目光俯瞰大地。與這篇散文對應(yīng)的是一張拍攝于內(nèi)蒙古草原的圖片,圖片上一只大鳥從草原上騰空而起。圖片中漸行漸遠(yuǎn)的飛鳥和茫茫草原之間的對比張力,不正象征著散文中所表達(dá)的哲學(xué)精神和世俗享樂之間的格格不入的關(guān)系嗎?
萊辛曾在其文藝?yán)碚撁独瓓W孔》一書中強調(diào)詩(泛指文學(xué))與畫之間的區(qū)別,認(rèn)為詩具有比畫更大的藝術(shù)表現(xiàn)空間,他指出:“如果繪畫一定要和詩藝做姊妹,她就不應(yīng)該做一個妒忌的姊妹,妹妹自己不能用的一切裝飾,她不能禁止姐姐也一概不用。”反觀陸永建的《飛翔的痕跡》,詩與畫的姐妹關(guān)系可以說是十分和諧的。構(gòu)建這種和諧關(guān)系的關(guān)鍵,是作者深刻哲思的統(tǒng)率作用:讓詩化的語言和精美的圖像合二為一,并得到一種情境和思想上的有力提升。譬如,在重慶的一座佛像前,作者不像一般游客那樣走馬觀花,或者表達(dá)一些“某某到此一游”的淺薄感受,卻由此游目騁懷,聯(lián)想起西方圣哲蘇格拉底的一段哲學(xué)公案,并引發(fā)這樣的反思話語:
蠟做的蘋果,怎么能聞到香味呢?因為老師的權(quán)威,因為經(jīng)驗和成見,因為普遍共識。
人性的弱點,就是迷信權(quán)威、懶于思想,人云亦云,憑經(jīng)驗、以成見下結(jié)論,結(jié)果用錯了人,歪曲了事實,危害了社會。
沒有思考,就沒有思想;沒有思想,就沒有哲學(xué)。
在物欲橫流的時代,哲學(xué)雖然就在我們身邊,但又離我們很遠(yuǎn)。——《蘇格拉底的蘋果》
正是這些深刻的反思話語,讓這篇散文的文學(xué)語言和相應(yīng)圖片的攝影語言找到了一個很好的結(jié)合點。文學(xué)語言和攝影語言的這種結(jié)合方式,我們在《夕陽五彩灘》《遙遠(yuǎn)的交河故城》等文與圖中也可以找到有力的印證。
總之,《飛翔的痕跡》一書中思、詩、畫的結(jié)合,充分體現(xiàn)了作者在當(dāng)代漢語散文文類探索上所作的一些努力。這種探索的核心,就是以一種開放的態(tài)度去發(fā)掘文學(xué)語言的種種藝術(shù)可能性。尤其是在電子傳媒技術(shù)突飛猛進(jìn)的今天,文學(xué)不斷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文學(xué)的類型之間的界線也日漸模糊,正如韋勒克和沃倫所言:“現(xiàn)代的類型理論明顯是說明性的。它并不限定可能有的文學(xué)種類的數(shù)目,也不給作者們規(guī)定規(guī)則。它假定傳統(tǒng)的種類可以被‘混合’起來從而產(chǎn)生一個新的種類(例如悲喜劇)。它認(rèn)為類型可以在‘純粹’的基礎(chǔ)上構(gòu)成,也可以在包容或‘豐富’的基礎(chǔ)上構(gòu)成,既可以用縮減也可以用擴(kuò)大的方法構(gòu)成。……現(xiàn)代的類型理論不但不強調(diào)種類與種類之間的區(qū)分,反而把興趣集中在尋找某一個種類中所包含的并與其他種類共通的特性,以及共有的文學(xué)技巧和文學(xué)效用。”面對當(dāng)前文學(xué)發(fā)展的新形勢和新問題,一位有追求的作家自然會敏銳地作出自己的回應(yīng)。陸永建先生正是這樣的一位作家。具體而言,他對于“攝影散文”的努力探索,可以說是豐富當(dāng)下文學(xué)類型的一種有益嘗試,值得引起我們的關(guān)注。
(作者系福建師大文學(xué)院教授、福建省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副主席)